番国质子牧云笙进京十多日,与皇太孙的关系已成为宫中秘闻。高秉烛沿着宫墙根儿行走,脚步轻的像猫,面色又像鬼,侍女见了相互私语两声,纷纷避让开来。
他拿了进内庭的牌子,来找朱瞻基。
皇太孙已经加冠,但仍然像儿时一般坐在圣上脚边,等着被考教兵法,或是哪里发灾误了农时,又或是有没有倾心的姑娘。高秉烛立在阶下,听不到殿中祖孙闲话些什么。他习惯性得扫了眼身后,见一人长相素白、怀抱两卷画轴,身后只跟了个书童,匆匆向远处走。想来便是质子牧云笙。
此处位于皇城东隅,高秉烛从申时三刻一直站到日头远远缀上屋脊,一排鸱吻映出圈毛茸茸的金光。宫人推开殿门,圣上的眼神在高秉烛身上停留一瞬——皇太孙手底下这些动作,瞒不过也无需瞒他。高秉烛心口一跳,只觉得自己被剖透了。好在朱瞻基大步流星地走下来,捏了捏他绷紧的肩膀。
“瘦了。”朱瞻基说。
一月未见,他也没有多出几句拉拢人心的话来。高秉烛不言语,从怀里掏出一封带血的名录。朱瞻基带着他向寝宫走,指尖捻了捻这张细薄的纸,微微蹙眉。
“不是我的血。”高秉烛低声道。
朱瞻基这才展颜,再次向他伸出手,一派兴致勃勃的神色。高秉烛抬眼看他,从怀里又摸了摸,拿出一个油纸包递去。
“卖豌豆黄的小贩都在议论牧云笙。”高秉烛说。
一个小国质子,风雅志趣再相投,朱瞻基又能得到什么助力呢?诚然,皇太孙有一瓣心来金风玉露,他也曾极短暂地得到过。但牧云笙的受宠这般声势浩大,背后必然有朱瞻基的默许乃至推动。
高秉烛想不明白,许多事不明白就罢了,他这一生关心的事很少。但他还是当面提起,生硬又突兀,朱瞻基略显惊诧地看了他一眼。
这一眼可以有好些含义,最多还是对高秉烛如此僭越的不解,却没有责备。他的话像不经意间的陈述,并非问题。朱瞻基不置可否,拆开纸包咬了口豌豆黄,含糊地回应道:“不过是虚名,能让他在宫里过得舒心些,不至处处受人冷眼。”
意料之中的回答——朱瞻基是有些偶尔泛滥、无伤大雅的好心肠。
高秉烛没再说其他,躬身告退。他不大想踏入朱瞻基的殿门,在肃穆堂皇的宫中呆了一下午仿若受刑。若是进去,皇太孙以待友之道请他坐下,请他饮茶,请他对弈,都更令人痛苦。朱瞻基知道与不同的人如何相处,极爽快地给他指偏路出宫。他已是将我看透彻了,高秉烛想,我却只识得他一面。牧云笙揽着画轴的背影又不合时宜浮现出来——他们交谈时,朱瞻基是什么样呢?
他逃也似的离开皇宫,即便清楚很快还会再来。朱瞻基需要他,当作从自己双手延伸出去、观察京城的触角,也需要他当切掉毒疮的一把刀。
“我瞧他不像一把刀。”牧云笙道。他亲自举着一把伞,遮住两人头顶,声音低低融化在雨里,“倒像片碎瓷。你从哪找来这么个心腹?”
永乐二十二年春,朱高煦与侄子之间的暗流愈发汹涌。牧云笙身处深宫,日日舞文弄墨、闲云野鹤。他每旬都能看到高秉烛入宫,不高调但分外惹眼,无人不知道他是皇太孙的人。可等高秉烛出了宫,如河入汪洋,没有一点踪迹。汉王想必每日恨得牙痒。
不知今日高秉烛带来什么消息。他走了一刻钟,朱瞻基仍杵在原地淋雨,面含薄怒,侍人远远站着窥看,不敢上前。牧云笙要了把伞,把人都遣走,自己走过来搭话。
朱瞻基张了张嘴,想反驳高秉烛不是他找来驱使的下属,却根本找不到其他说辞。牧云笙聪慧,不能一两句话敷衍。他如实道:
“京城年节里放河灯,我换便服出宫,遇到他。”
那晚高秉烛穿得像个破落乞丐,脸消瘦苍白,一双眼烧着火。朱瞻基为他放了三盏河灯,祝他长寿、康健、来年仍能有愿景。他隐隐觉得高秉烛有寻死的念头,便拉对方一同喝酒,半醉时一脚踏进河里,反而被高秉烛捞出来,慌慌张张擦他脸颊上的水。他们的脸和手都是滚烫的。
雨下得又急又密。牧云笙悠悠吐出一口气,弯起眼睛笑:“谢殿下解惑。”
牧云笙心情罕见得不错,兴许是因为听到了问题的答案,又把这惑转送给朱瞻基。数年为质,他旁观了朱家无数腌臜事,看久了得一份别样的热闹乐趣,像只笼里被养得很好、坏心眼的猫。
春夜寒凉,朱瞻基心绪纷呈,未留意牧云笙的反常。
七月,帝王驾崩的消息从蒙古裹挟着暑热秘密传至皇城。
一时间几方势力都有些按捺不住。数十天里,朱瞻基与高秉烛没睡过一个整觉。宫里宫外,王府臣门,全都各怀心思。直到八月朱棣遗诏送至京城,皇太孙也基本稳定了局势,便要亲自离京迎丧。
高秉烛留在京城,暂做几日市井闲人避风头。
一切都平稳地运转着——皇太孙即将扶棺回城,宫中紧锣密鼓着筹备新帝的登基大典。突变陡生那夜,高秉烛正在一家小客栈里难得睡个好觉。
尽管开始就被蒙了眼,高秉烛也很清楚是谁的兵。朱高煦许是摸不清他知道多少事、在朱瞻基心里又是何地位,所以他们还算得上客气,绑完拳打脚踢了几下,没见血。
他被连拖带拽从后门出了客栈,心里暗自一个个滤着究竟谁卖了消息。朱瞻基明日才能回来,怎样提醒他防备。没等他想完,拐过两个小路,就又被劫了。
缠眼的布条解开,高秉烛认出是镇抚司朱瞻基的亲信。
“殿下提前一天回城。”对方简短地说,“宫中有变。”
这一小队人马杀人毫不手软,没留下给汉王报信的活口。他们护送高秉烛到城南另一落脚处,急急离去了,没有透露更多消息。
一周后高秉烛才收到信鸽,邀他入宫。
他换了身干净的粗布衣服,将自己收拾得整齐些。见到朱瞻基时反而吓了一跳——朝中人人心知肚明,他被封太子就过几日的事。而未来的太子头发也未束,眼下乌青,只穿着白色里衣坐在桌案旁作画。
纸上压着一砚墨、一碗酒。高秉烛走过去坐下,喝掉了那碗酒。
“你现在倒不拘谨了。”朱瞻基笑笑。
“殿下身上没有酒气。”高秉烛答。
朱瞻基盯着他定定看了会儿,突然道:“牧云笙被秘密处死了。”
高秉烛四平八稳地坐着:“外面的消息是暴病而亡。”
朱瞻基点点头:“对外是这么说的……”
离乡十载,牧云笙与故国并未断了联系。他在明宫中运筹边疆战事,国丧之时浑水摸鱼,勾结朝堂逆臣。朱瞻基扶丧回城当晚,将其一并诛杀。遗体收敛,送归来处。
刀架在脖子上时,牧云笙面色平静。他问朱瞻基这些年到底喜爱他些什么,至于如此好心帮他造势,让一个质子过得风生水起。
明宫里他至多是臣属身份,君对臣的喜爱,究竟是知音流水,圣王贤相,还是豢养一只看得过眼的小宠,总不会很分明。朱瞻基说,爱他自由,爱他丹青,牧云笙觉得可笑,又暗自有些清高的得意。
高秉烛才是真的自由,他想,但朱瞻基便是这样,轻易让荒狼变成家犬。又这么随随便便让自己这养不熟的灾星尝过金杯,欣然引颈就戮。
事发种种,朱瞻基几句言明。高秉烛听罢攥紧了手,骨节微微泛白:“所以七月一得到消息,你便让我赶去私下换防。”
“防患于未然,我那时也不能笃定他会出手。”朱瞻基垂着头,声音放得很轻,故而高秉烛看不到他的神色,也琢磨不透他的心情。“他做的事,不管成了还是没成都不能活。”
其中弯弯绕绕,高秉烛略一思索便清楚。牧云笙知其不可为而为之,是没有别的选择。他把活着的最后一刻都献给故土。剩下能做的只有将自己的死亡交给朱瞻基。聪明人的情意上了秤,每一分都精细的另有所图。这方面想来,牧云笙与储君是同一类人。
“还有……他最后让我速派亲卫救你。”朱瞻基道,“二叔兴许认为他是个绣花枕头,没多防备,让他得了消息。”
高秉烛之前每次进宫,并不都能看到牧云笙。这位小国皇子总穿着华贵,只关心书画风雅。一看便是锦绣堆儿养出的玉人。故而虽然与他面容有七分相似,两人站在一处,也不会有人说相像。牧云笙猝然死了,还有更多人悄无声息地死在这个夏天,成为被皇权刈下的一粒麦。
还好,万幸,幸中之幸,朱瞻基还在,还有一双湿润的、少年般的眼睛。他倾过身子,握住高秉烛的手腕,低声请求:“二叔的事解决之前,先住在宫里吧。”
阳光从窗格漫进来,淌过桌案上平展的画纸,上面两只狸奴睁着圆鼓鼓的眼睛。高秉烛移开视线,逆着光看窗外簌簌作响的槭树。京城夏天的风带着一股尘土味道。
先帝灵柩前,汉王是否动了手,朱瞻基没说,高秉烛便也不问。爷爷走了,皇太孙身上一些东西也跟着永远消失了——譬如偶尔孩子般的娇纵无畏。
他不再去想失去和得到。太累了,牧云笙想必也活得累。何况牧云笙囿于命数。天下人对他很重,从小到大锁在他颈上,对他也很轻,不如新画一笔浮墨。高秉烛却是淤沼里长出的草木,活着本身已经令人难以忍受。昼短苦夜长,为一刻的休憩、一刻见皓月如银,高秉烛便将自己熄灭在夜里。
“谢殿下。”
他低眉敛目,任由朱瞻基握着。听他轻叹一口气,将手中笔杆顶在高秉烛胸口,点了点,道:“我的心。”
我知道。
高秉烛心说。
可我真得知道吗?
汉王一直就梗在那里,成为不硬不软一根刺,所谓的“事情解决”看起来只是句空话。几个月后朱瞻基受命启程去应天府,走前写信给高秉烛——他的烛苗似乎彻底成了暗夜里的影子,太平时候几乎不与他见面。朱瞻基不愿以太子身份压他,只好听之任之。
父皇有迁都之意。
可愿与我一同在金陵放河灯。
又絮絮写了些别的,朱瞻基扔下笔,捏了捏眉心,无缘无故想起牧云笙的话。碎瓷怎么去修补,牧云笙若知道朱瞻基现今为此所累,定要笑个三日三夜。
他第二日启程。高秉烛来去如风,若是愿去,自会在应天府见面。
太子的小愿望不出意外落空了。高秉烛留在了皇城。每过一旬他都收到朱瞻基的亲笔,不涉政事,只闲话些金陵繁华盛景,十里秦淮。高秉烛一一收存,未曾回信。
对朱瞻基来说,安稳日子总不会太久。
未过一年,太子在南京收到皇帝病重、召他回宫的密令。朱瞻基日夜兼程,行至途中接到高秉烛送来急报,得知汉王意欲截杀他以自立,最终有惊无险北上,入宫发丧。
接连失去祖父与父亲,朱瞻基被揠着向上抽条。没有时间了,他要在一夜之间成为遮蔽朱家天下的树,成为每个人举头三尺的云。高秉烛在小树下贪睡一晌,告诉自己,是该醒得时候了。
六月的顺天府天朗气清,宫中植的花不知忧愁,锦簇开着。高秉烛频频想起那张狸奴画上一格一格柔软的阳光。他一直留到朱瞻基登基第二日,先行离开去了朱高煦的封地,潜入乐安城。
新帝得知后,对着北防军图,心不在焉,长吁短叹。
八月,朱高煦反。
双方对这一日都等了太久。朱瞻基直言要御驾亲征,朝堂哗然。他未多纠缠,召英国公即刻下谕。
此时高秉烛疲于逃命,浑然不知。
他送了很多消息回去,譬如叛军家眷尽在乐安城中,故而汉王不会冒险南下,又譬如何处太守与朱高煦勾结。几乎是带着一股自毁的冲动在敌营游走,也不出意外的被数次追杀。
这些朱瞻基不会知道,不需知道。长箭射穿高秉烛的肩膀那夜,他终于再逃不动,遥遥望过一眼北方,纵身跳入了护城河。
盛夏,水仍冰凉砭骨。他最后想起,永乐年间,朱瞻基瞒着圣上偷溜出宫,和他误进一座佛堂,满堂淌泪的明烛。他们没有跪拜,看世人求富求寿求姻缘求万千烦恼丝,再静悄悄退出来。他那时站在皇太孙身边,笑得好像已得了天地间第一称心如意事。
高秉烛很快失去了意识。
他醒来时好像已经死去。泡透了血水与护城河水的衣物被尽数换下,箭伤也上药包扎,躺在床上如卧云端。高秉烛勉强撑起身子,看到床尾烧着炭盆,他环视陈设,认出这里应是帝王的军帐。这不是他活着能梦到的场景。
不久便有人去通报,帘子被从外挑开。朱瞻基走进来,身穿一件软甲,从头到脚湿漉漉的寒气,像一株清晨挂满露水的松。帐外仍是一片灰蒙暗色。
“卯时了。”他止住高秉烛的话头,在床边坐下,眼底露出疲态,“你昏迷了两日。”
“陛下亲征,汉王请降指日可待。”
高秉烛阖眼,如是说道。
一瞬静默。朱瞻基伸手探探他额头:“醒来便说这些?”
他知道高秉烛没什么弦外之音,纯然说得真心话,所以才无奈。高秉烛的执拗只能自我开解掉,他什么也做不了。
“你被发现的河岸太荒僻,流民和乞丐都罕见。他们以为是细作,朕的亲兵认出是你,速来上报了。”朱瞻基道,“醒了就往里面让让,朕睡一刻钟。”
“宁王已不足惧,”高秉烛还是没什么力气,从磨破的嗓子里挤出话,“陛下无需太过操劳。”
朱瞻基笑起来,连带着高秉烛的心脏一同震动。政事不止军务与争权,他要自己做******,每一块血和肉都散在九州山河。但他只侧躺下来悠悠道:“有人占了朕两日床榻,朕无床可睡,只能衣不解带地看折子。”
听了玩笑话,高秉烛却挣扎着要起身,又被对方摁回去。
“莫要动,扰朕休息治你的罪。”
朱瞻基闭着眼睛。他确已困极,说话含糊不清,“以后时间还长。”
高秉烛翻过身,指尖碰碰朱瞻基的眉。传世之孙,永世其昌,那个万千宠爱的皇太孙,草原上撒蹄的马驹,顺天府神采灼灼的浪子,离如今才几年。他想说君无戏言,最终收回手,顺从得一同睡去。
文章来源:{laiyuan}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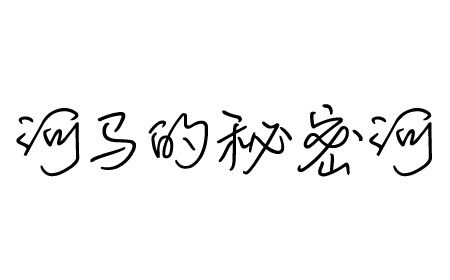
- 最新
- 最热
只看作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