楔子.
罗云熙挽起袖口,露出一截白皙透亮的小臂,走向墙面镜,没理会女学生们爆发出的一阵骚动,抬起胳膊旋转、跳跃,好像展翅的天鹅,从湖面凌入空中。
这是他安顿下来教芭蕾的第三年。
第一年舞蹈室刚建,没什么名气,他大冬天站街边发宣******,怕风大拿不住,不敢带手套,冻得直缩脖子也坚持给人赔笑脸。
也许是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,挨过一冬后,开始有学生陆续找上门,虽然多半都是单身小姑娘。
不管人家是不是醉翁之意,好歹碗有了,能吃上一口热乎饭。
罗云熙不求别的,这就够了。
就算长得再年轻再精致,罗云熙也过了三十。
青葱年岁过去以后,他心里没有多余地方摆放理想和热血,只剩下现实。
北方的冬日从来不是吹牛逼,出门大风一刮,哪怕是滚烫的热血,也能瞬间冻透。
在这里,不现实的人根本活不下去。
想当初他和陈飞宇大包小裹过来,正赶上立冬下雪。
到站火车门一开,西北风窜堂,一人赏了一个大耳刮,他们俩到了新家才缓过来。
陈飞宇一边剁饺子馅,一边问他适不适应,不行再搬。罗云熙和着面说不用,这地方挺好,有活着的感觉。
当啷一声,菜刀撂在木头案板上,陈飞宇回头揩掉他脸沾的面粉,说你要喜欢,这儿以后就是家了,咱俩一起好好活着。
罗云熙记得,那天陈飞宇一高兴,光饺子馅就和了三种,韭菜虾仁、猪肉白菜和牛肉香菇,最后包多了,扔冰箱冻着,过小半个月才吃完。
晚上收拾厨房时,他问陈飞宇干嘛包那么多浪费材料,他俩是来过日子,又不是开饭店的。
陈飞宇眨巴眨巴眼睛,挺委屈地说:“别人能吃上的,我都想让你吃上。”
上.
2003年,罗云熙二十三,一个人过惯了中秋和除夕,早忘了什么叫团圆。
过年放假,员工宿舍只剩他一个活人,他就躺在床上看三年前从家带出来的一本《青年文摘》,从初一翻到初七,要不是复工早,他能翻到十五去。
虽然包了书皮,但这么来回翻了三年,内里早就破烂不堪,缺页损角,挂在订书钉上摇摇欲坠,好比他这个人。
离远了看,光鲜体面,可身体里全是伤疤和口子,像件脆弱的艺术品。
他不适合被人拿起来端详、翻阅,他就适合安放在无人观赏的展厅,随时间一起流逝。
只有他自己清楚,裂纹不是天生的,从三年前才慢慢长出来。
罗云熙的老家东部,有一幢不起眼的灰色平房,夹在两条土路中间。
60平的房子格外拥挤,隔间加了又加,好不容易才能供屋檐下的八口人睡开。
罗云熙的爷爷奶奶住一间,爸爸妈妈住一间,叔叔婶婶住一间,他和弟弟则共住一个小隔间,上下铺。
为了正常生活,早晚使用厕所的顺序每天固定,上班的优先,上学的其次,退休的最后,纪律森严得像在部队。
那时候房子是租的,但自由并没受到产权的约束,日子就在弟弟每次睡梦中翻身,头顶床板传来的嘎吱嘎吱声中过去了。
2000年夏天,七月份中考放榜,罗云熙被他爸叫过去,门一关,满屋都是缭绕的二手烟。
在他愈来愈响的咳嗽声里,他爸夹着烟,抬头看白气一点一点升腾,触到起皮的天花板。
“你弟考上了。”
烟雾随着声音,从耳朵灌进罗云熙的嗓子,他肺里堵得慌,突然说不出话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,烟被掐灭,留下一地余烬,像一把快烧干净的头发丝。
他爸又说:“咱家没钱供两个人。”
那年罗云熙二十,无忧无虑了小半辈子,忽然被命运按住脖子,以铡刀裁决。
成年人忘性大,他爸似乎三番两次就忘记以前最爱叨咕的口头禅,但罗云熙还记得。
世上无难事,只要肯攀登。
可没钱往往是放弃一件事,还能免受苛责的最好理由。
罗云熙第一次对“没钱”产生深刻认识,是在他弟小升初那年。
同样是个日头很大的夏天,他爸带回三个小鸭梨,给兄弟俩一人一个,自己洗了一个回屋跟爱人分吃。
俩人闭门商量一下午,第二天带他找老师停了兴趣班。
罗云熙的芭蕾舞老师姓邵,有酒窝,长得漂亮,是他妈妈朋友的表妹。知道他家情况不好,就把学费打了对折,让罗云熙跟着跳了十二年。
同一时期,别的小朋友几乎都在学钢琴、书法,因为价钱,罗云熙学了芭蕾。
也是因为价钱,他又不得不放弃芭蕾。
临别之前,邵老师翻出一双新芭蕾舞鞋,追到门口送给罗云熙,长长地拥抱了他:“没事小罗,你很棒,相信自己。”
夕阳洒下来,把他们染成红色,镀上一圈恩慈的光。
她又说:“别灰心。以后掌声会响,灯也会亮。”
决定办退学手续的前一晚,罗云熙翻出那双芭蕾舞鞋,上面落满了灰。
他想起第一节芭蕾课上,全班就自己一个男生。
邵老师把他拉到身边,在女生们投来的奇异目光里,告诉大家芭蕾是一个美好的梦,谁都有权利向往,不分性别,人人平等。
这片段不长,在脑海中短暂闪过又消失。
罗云熙蹲在地上,安安静静给鞋擦灰,深一道,浅一道。
他忽然鼻子一酸,觉得不是鞋,而是自己的梦积了灰。
不再美,也不再好。
狭窄的房间里,弟弟经过他身边,不小心挡住棚上吊灯,黑色的影子盖在罗云熙脸上,像突然降下的长夜。





![表情[liulei]-河马的秘密河](https://hema66.cn/wp-content/themes/zibll/img/smilies/liulei.gif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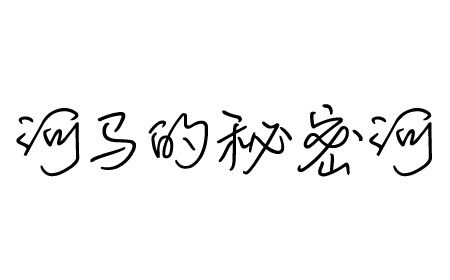
- 最新
- 最热
只看作者